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楼婍沁
美国加征关税带来的影响仍在中国制造业蔓延,其中纺织服装是受影响较大的一个行业。
“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弄,跟以前不同。”服装供应商胡风对界面新闻说。他所运营的公司曾是多个跨境电商平台的供应商,如今主要承接国外服装品牌的贴牌外贸大单。
目前在其公司业务中,出口美国的订单占比约一半,另外一些出口给欧洲品牌的商品,很大一部分销量也在美国。所以美国对中国和欧洲加征关税,都对其公司业务造成不小影响。
美国是中国纺织服装出口的第一大国家。根据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的数据,2024年中国纺织服装的出口额达3011.3亿美元,其中对美出口达509.6亿美元,占比16.9%。美国也十分依赖中国的进口,2024年美国来自全球的纺织服装进口额中,中国所占份额达到26%。
4月以来,美国政府持续抬高对中国输美商品的加征关税。到4月10日,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国输美商品征收“对等关税”的税率进一步提高至125%,加上此前以“芬太尼问题”为由定下的20%关税,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累计已达145%——至此这更像是一场“关税数字游戏”。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在最新公告中表示:“即便美方继续加征再高关税,已经没有经济意义”。

观望是行业里的普遍态度。
胡风认为,现在的高关税状态肯定不会长久维持,要看接下来两国何时能谈妥。
“客户会观望一段时间,如果中美能解决,固定好条件后,订单就会暴涨起来。”他说。
胡风告诉界面新闻,如果能将税率能谈到一定范围内,是可以被接受的,这部分增加的成本可以由客户、供应商、物流、汇率等多个环节来分担。
也有一些供应商尝试另寻出路,例如通过转口贸易以第三国作为跳板,暂时避开高关税。4月10日,美国宣布对未采取反制举措的国家暂缓高额“对等关税”90天。
界面新闻注意到,不少提供类似业务的服务商已经在多个社交平台上打广告、招揽生意。
但胡风认为,向其他地区转移订单也不是长久之计,重要的是能否找到新的订单。
让不少人意外的是,有一部分外贸工厂在当前背景下,爆单了。一些来自跨境电商平台的大量新订单正在涌入这些外贸工厂。
在广州番禺,为某跨境电商平台供货的供应商蒋义向界面新闻表示,他的工厂处于爆单状态,“最近忙晕了”。据他讲述,附近的一些外贸工厂也是类似情况,“周边的厂只要是开着的,都还算比较火”。
在此轮美国关税政策调整中,与跨境电商平台相关的主要是小额包裹(800美元或以下)免税政策。这个红利也是此前中国跨境电商能以有竞争力的价格打入美国市场的原因之一。
而在4月3日,美国政府宣布,将于美东时间5月2日起取消针对中国内地及香港的小额包裹免税政策。截至4月11日的最新规定是,在5月2日至6月1日前,美国将对每件小额包裹征收其价值120%或每件100美元的关税,6月1日起征收每件200美元的关税。
鉴于该政策尚未生效,外贸工厂爆单或许也与平台想赶在窗口期备货有一定关系。
蒋义认为,他的工厂及附近的工厂之所以能爆单,主要还是因为客户和工厂都相对有实力,前者能提供订单,而后者能被分配到订单。对于蒋义而言,他的大客户是那些跨境电商的头部供应商,他们能争取到体量大、单价高的订单,再分包给下面的其他工厂。
但他也提到,生意越做越旺并非服装外贸行业的普遍情况,也有工厂在过去几年生意下滑,逐渐被市场淘汰。

实际上,在加征关税前的过去几年里,中国的服装外贸市场竞争已经相当激烈。一些原本从事外贸生意的供应商面临订单量下滑、利润空间缩窄的情况,因而收缩了这部分业务。这使他们在这次的关税风暴中躲过一劫。
一位广州的服装供应商告诉界面新闻,他的工厂并没有直接的美国客户资源,而是通过贸易公司获得出口订单。从2024年开始,他们接到的美国订单已经在下滑,价格也在往下压,“往年假设是10块钱的单,今年被压到8块。本来就没有多大的利润,是跑量的,很多已经没有什么做头。”
据他讲述,他所在的番禺南村镇塘步东村,在过去两年里有大约四五成的工厂因为缺少生意而关闭。番禺南村是广州服装制造厂的聚集地之一,外贸订单较多,如SHEIN等跨境电商的不少供应商都在这里。
另一家位于苏州的男装供应商也是类似,主要通过贸易公司来做外贸生意。但与贸易公司的合作也有风险,该供应商就曾被弃单,导致尾款未能收回,此后便不再有很强的意愿做外贸生意。
即便是能直接与外国客户达成合作,位于国内的供应商也相对被动。
在杭州四季青设有档口的衣诺倍思服饰告诉界面新闻,疫情前还有欧洲、澳洲的客户前来选款,他们能贡献较大体量的订单,但通常一年只来两季,未能保持长期联系。过去几年,该供应商的外贸业务从此前的占比30%下滑到10%。

事实上,中国国内的服装市场也长期处于饱和状态,淘汰赛一直在进行中。
塘步东村某工厂的员工告诉界面新闻,她所在的工厂现在基本只做内销订单,而过去几年里工厂面积从此前的两三千平方减少到几百平方。“以前生意好到根本没有时间扯废话,就是打包、出货。现在要讲服务、(利润)透明,客人想要商场货的品质、出厂价一样的便宜。”
界面新闻记者见到这位员工时,她正在村口旁的街边甩卖工厂里的库存服装。据她讲述,常有人上前问她是否招人,而实际上她所在的工厂也只有干得久的骨干员工才能留下。
这与服装产业链向内陆迁移也有一定关系。
在广州番禺从事纺织服装业的不少劳工来自江西和湖北,过去几年里随着人口回流,一些产业链也随之迁走。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北方,前述苏州的供应商也告诉界面新闻,近些年江浙地区一些服务B端客户的供应商也在向江西、安徽、山东等地迁移。
另外,电商平台的监管政策也抬高了内销市场的竞争门槛,促使商家们提高自身水平。一位杭州供应商告诉界面新闻,如今电商平台对仿大牌的logo设计查得更加严格,增加了竞争难度。
中国的服装商家向来对内销和外贸市场的竞争压力有所体会,并一直尝试在变动而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摸索生存法则。某种程度上这增强了参与者的韧性,使他们在面对高关税等极端情况时,仍有灵活应对的心态,同时积极找寻新的可能。
成为大型时尚品牌的供应链成员是不少供应商的愿望,这些品牌能提供相对稳定的订单,能让工厂过得“不那么卷”。但门槛也相对较高,例如对工厂的规模和智能化程度有一定要求。
借由直播电商转向C端生意也是一个出路。前述苏州供应商告诉界面新闻,他们现在从过去服务B端客户转向服务小B端和C端零售,目前精力主要放在维护这块业务上,暂不考虑开拓外贸业务。
专注于外贸生意的胡风则向界面新闻表示,他已经在不断寻找其他地区的客户、落地新的订单,“这个时候更要进取。”
一些尚未被充分开拓的新兴海外市场正在吸引着像胡风这样的外贸商人。
胡风表示,相较于中东和东南亚这种已是红海的市场,如澳洲、欧盟、印度、南美等市场还有机会。另一位主要承接国际时尚品牌订单的供应商也告诉界面新闻,他们也在观望目前的局势,未来或许考虑到北非或中欧开拓新市场。
(应受访者要求,胡风、蒋义为化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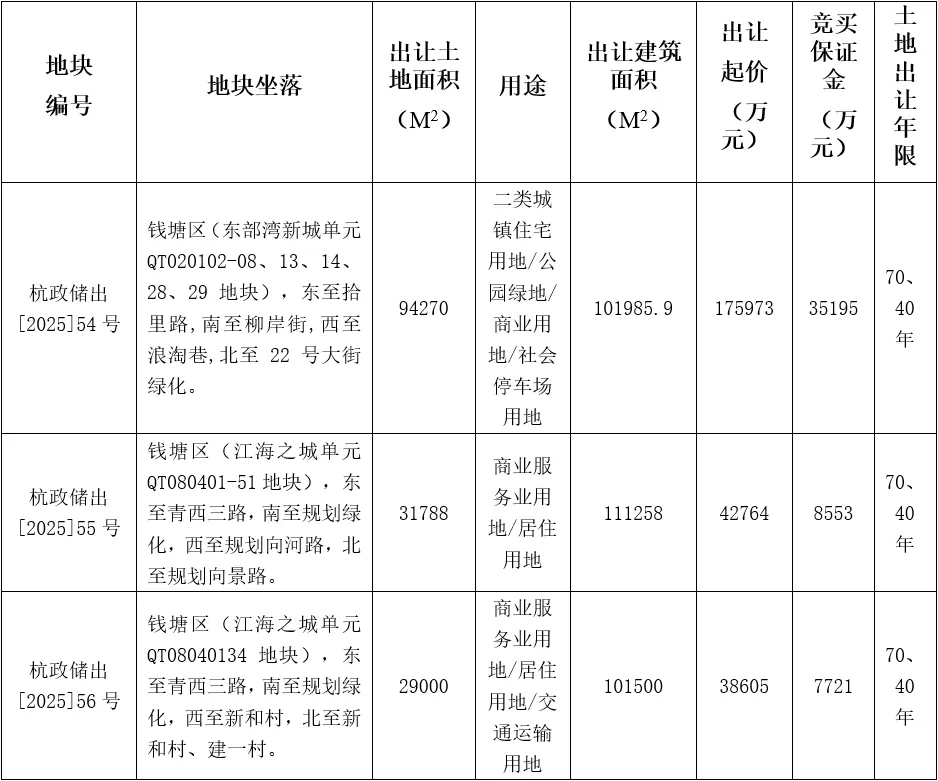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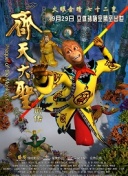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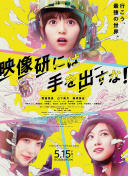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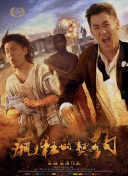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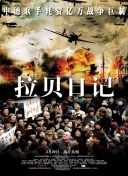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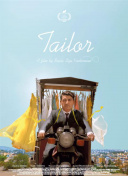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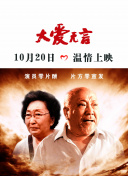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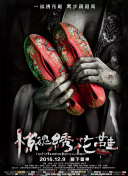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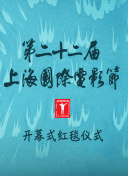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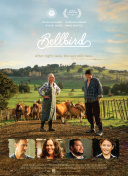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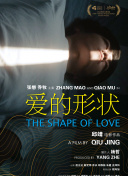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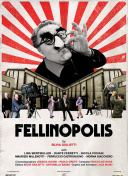
 47847
4784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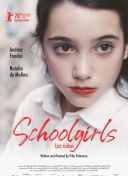 26
26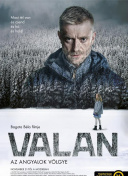


 47847
47847 26
26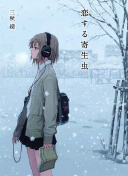


 48158
4815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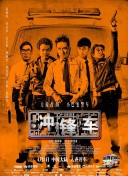 46
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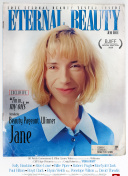 18095
18095 59
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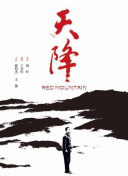 76276
76276 17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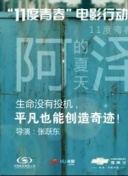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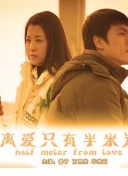
 65573
65573 36
36


 63128
63128 4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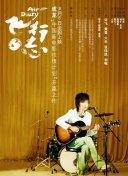

 86478
86478 85
85


 30367
3036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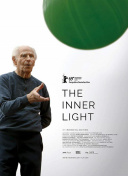 78
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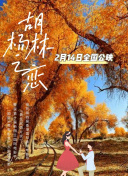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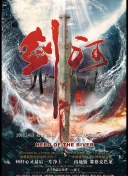
 63524
6352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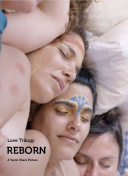 2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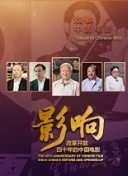

 62738
62738 4
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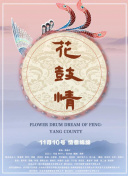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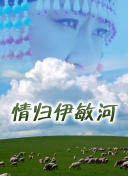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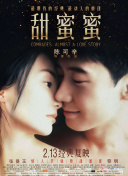 31856
31856 47
4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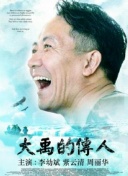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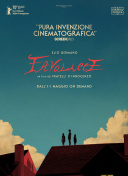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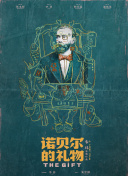 71272
71272 50
5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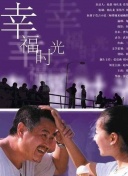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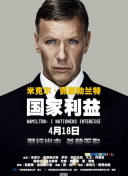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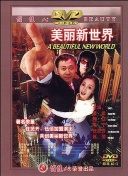 83067
83067 20
2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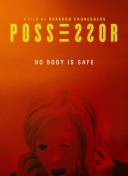


 99712
99712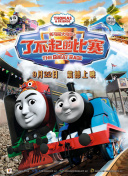 97
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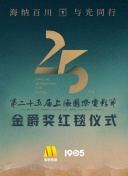

 54978
54978 31
3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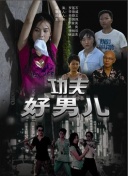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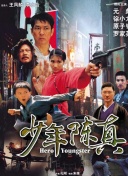

 63720
6372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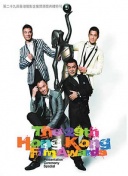 90
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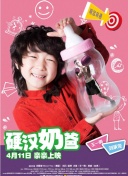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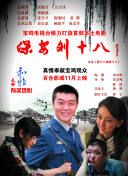
 94331
94331 53
53


 29063
29063 54
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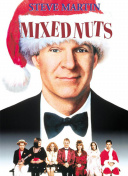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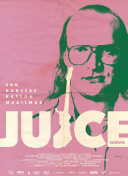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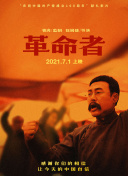 68942
68942 21
2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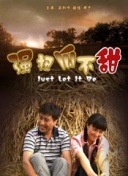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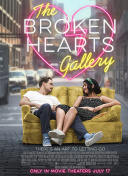 89181
8918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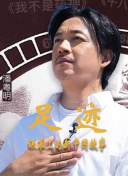 94
94


 23218
23218 58
58


 28745
28745 52
52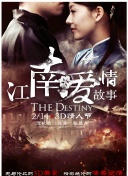


 81201
81201 44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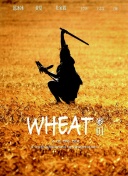

 17391
17391 69
69


 29549
29549 6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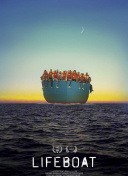
 17480
17480 70
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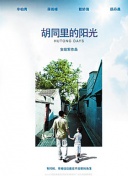 89028
89028 4
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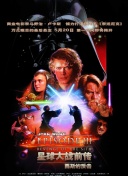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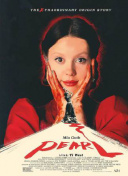
 98746
98746 88
8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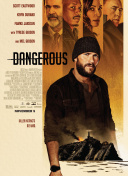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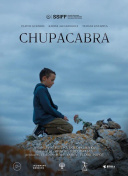
 79267
79267 68
6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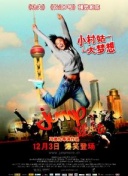


 83517
83517 81
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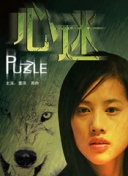

 27017
27017 78
7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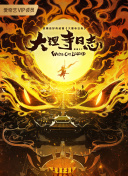


 54410
54410 77
77


 62398
62398 1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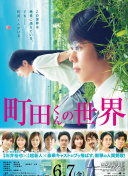
 63428
6342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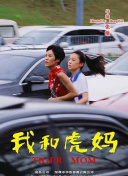 58
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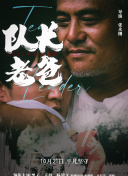 63473
6347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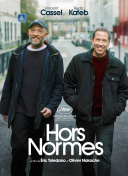 31
31


 47199
47199 19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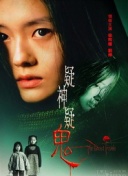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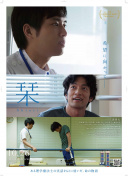 84052
84052 15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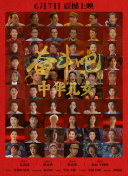 46245
46245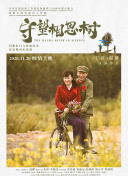 22
22

 19684
19684 80
8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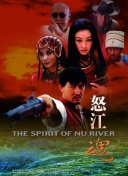

 22271
22271 49
49


 94874
94874 50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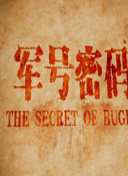
 36152
36152 35
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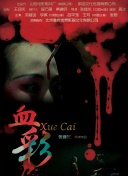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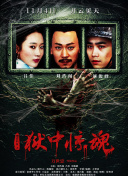 45060
45060 29
29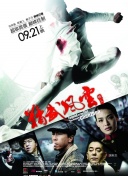


 74946
74946 99
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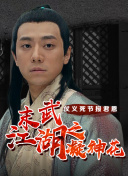 90160
90160 42
42


 41857
41857 2
2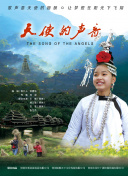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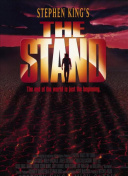 8
8


 47534
47534 52
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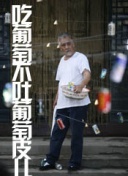 61701
61701 41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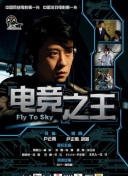
 52980
52980 33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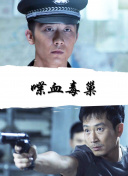

 50061
50061 60
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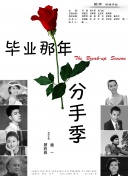
 68054
68054 69
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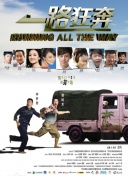
 93840
9384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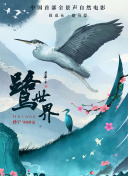 53
5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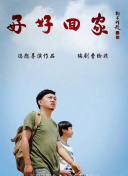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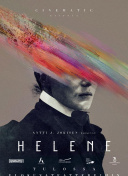 92885
92885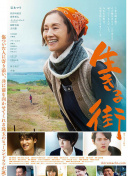 11
11